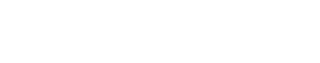2019年7月7日至11日,在为期五天的调研中,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三下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团队往返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周边城镇、探访了凤山石砚传承人钟健、胡呐喊传承人熊节仁、大郁竹艺传承人周友帮等六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每天上百公里长途跋涉中,始终陪同调研小组下乡调研的、对每一项非遗项目都如数家珍的、与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联系密切的,就是桃江县文旅广体局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刘勇华。

每一位非遗传承人在见到刘勇华主任的时候,都会亲昵地拍拍肩、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在讲述中时不时地将目光投向他以寻求肯定的点头……不难看出,刘勇华对于桃江县非遗传承人,早已超越了公事公办的例行关心。事实上,相比某一项目的传承人,非遗保护中心的刘主任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广更深的见解。因此,7月11日,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团队对桃江县桃江县文旅广体局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刘勇华进行了专访。
面对曾经在山西当兵多年的刘勇华,调研团队最好奇的,便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为何选择从事温吞细碎的非遗保护工作。“我自己喜欢嘛”,刘主任笑着说,“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很热爱我们的文化。”说到这里,刘主任叹了口气:“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很多小时候的手艺消失,但直到接触这一行,我才意识到,那些不起眼的手艺都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我国正式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2006年就参与非遗保护的刘勇华无疑是非遗保护的排头兵。从事非遗保护已经多年,在他见证下重获新生的非遗项目不在少数,但他最记忆深刻的,却是一位后继无人的非遗传承者弥留之际的那句“没人传承,我死都不瞑目”。说到这里,刘勇华默默转开了视线,眼睛有些发红。沉默了许久,他说:“我们听着都想哭啊。”
一开始,调研团队只是把刘主任看作文化部门的管理者,感谢他在调研过程中的陪同与帮助。而当刘勇华主任红着眼眶说出那句“我们只是非遗工作者,作为个人我们没有能力保护非遗”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刘主任对非遗的热爱和对非遗逐渐失传的无奈。

刘主任在专访过程中强调了:非遗保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毕竟经济支持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来说是基础保障,许多非遗项目缺少传承人的原因很大程度便在于其经济效益的低下,而个人对传承者的寻觅以及培养往往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导就愈发重要。
刘主任以舞凤山石砚为例,例举了非遗传承中的种种困难:为了给舞凤山石砚寻找传承人,钟健就将目光投向了特殊学校的聋哑学生,一些学生在技艺的学习方面具有“不容易受外界干扰”的优势,可以为特殊学校的学生融入社会生活与生产提供新的思路;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部分特校学生也存在情绪较易激动的现象,在与尖锐工具接触时便存在较高的隐患。

调研期间,团队走访了国家级、省级、市级三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什么项目才能被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刘主任告诉我们,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这是需要申报和评判的,不能够自我判断;其次,要具有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有着鲜明的特色、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最后,非遗项目需要在一定的群体或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以活态存在,已经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项目不能够被认定为非遗。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怎样被发现、被申报的呢?刘主任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逐层递进的过程:在乡村设立的文化站每年向县里申报非遗项目,县级单位择优评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年后市级单位再从各县择优评选……以此类推,一直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每一项究竟最终能够被评为哪一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确定的。
对于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支持的力度自然有所差别:小郁竹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申遗成功后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期间,曾收到两次数目为几十万元的经济支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是每年都会进行经济支持的了,对于湖南省来说,这笔经费更是大部分都集中到了湘西;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支持就更少了;而在实际落实的地方县政府来说,经济状况较好的县会自行拨款给非遗项目,但桃江县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虽然钱少了点,”刘主任的脸上露出些许的尴尬,“但给一点经费,好歹是一种鼓励,起码心没凉。”

“政府除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是否采取了将非遗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面对调研团队提出的非遗产业发展问题,刘主任比较乐观,他提到安宁水库旅游区设置了大栗港胡呐喊的表演,高亢的声音常引人驻足,此外,竹海景区的擂茶也是成功的典范。
“但这种产业的结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保留非遗的精髓。”刘主任特别强调道。也就是说,对于注重雕刻技艺的凤山石砚来说,将雕刻的精髓从砚台转移到茶案上来,是一种产业的创新;但对于追求纯粹高腔艺术的胡呐喊来说,加入平腔的元素则不被接受。这就要求非遗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特点来合理规划。
对于埋头钻研技艺的匠人们来说,这并非易事。“老艺人都是坚守了一辈子的,为什么?不为别的,就是爱。”刘勇华主任简单而质朴的一句话,真真切切地道出了每一个非遗工作者、每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内心。

在专访的最后,调研团队有人轻轻地问道:“除了我们,还有人来过吗?”
“来过,中央电视台都来过,呆了好多天。播出了,将近30分钟的胡呐喊宣传片。有用吗?没有。”
“那您还会对每次采访都抱有期望吗?”
“哪还有什么期望。”说到这里,刘主任却悄悄背过身抹了把眼泪。
充满失落的言辞的背后,一定还是有着热切地爱与期望的吧,不然又怎么能够这样孤独地守望多年。

谨以此文向以刘勇华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致敬!
责任编辑:金理琦
注:转载该文请注明来源:湖南大学新闻网